路时中,子当可,符箓派抓鬼大师,北宋末年便已声名远播。各级官员对他也是闻名遐迩,算得上当时跟政府走的最近的宗教人士。
路时中是一个热爱周游四方的方士,不仅拥有抓鬼通灵的本事,更习惯于帮助地方官解决超自然案件,也就是“鬼案”,他的名气也是由于帮很多官员侦破了无数“鬼案”,以至于广为人知,当时的人甚至还给了路时中一个雅号——路真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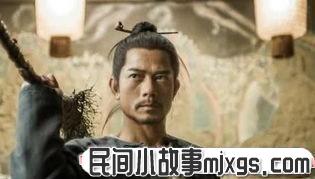
建炎元年,也就是南宋开国的第一年,这一年路时中离开前都开封,东下至安徽省灵璧县,并将船停在了灵璧县南的淮水之上。
当时国家初定,很多地方官员都属代职,灵璧县的县令,是也临时代理,姓毕名造。此人听说路真官游历至此,立刻跑出府衙,直奔江边,欲见路真官一面。
路时中听说是官员求见,知是定有“鬼案”,于是准见。
毕造行完礼数,开口说:“我家的二女儿,被鬼祸害,找了好几位道人法师,都反被恶鬼殴打谩骂,现在小女越发严重,我想除非路真官出手,否则我女儿是必死无疑,若是您不嫌弃,我可以马上将女儿带到您的面前,你看如何?”
路时中本就是抓鬼术士,鬼怪之事理当过问,于是痛快答应。
毕老爷得令,转身出去,命家人将二女儿抬进船舱,放在了椅子上。
此时的二小姐双目紧闭,处于深度昏迷,俨然朝不保夕随时断气的架势。路时中一看,便知是鬼祟上身,于是打算用法。
正在路时中将要法力之时,只见那二小姐突然睁开了眼睛,随后站来起来,动作流畅,宛如常人。
二小姐起身后,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然后向路时中进行大礼叩拜,拜完,站在了一旁。路时中间此鬼如此礼貌,决定先不动手,貌似鬼魅有话要说,于是同舱中诸人一样,目不斜视的盯着她看。此时的二小姐神色圆润,有如常人,脸上还泛起了一丝喜悦,真叫人无法同刚进舱时的她相提并论。

满舱中,除路时真跟毕二小姐外,其他人都以为是路真人法力强大,鬼怪望而生畏,已经离开,又见小姐笑容,诸人不觉也有喜色,可惜的是,他们都高兴得太早了,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诸人的一切喜悦,都伴随着二小姐的开口说话,瞬间烟消云散了。
二小姐说:“我乃毕家大小姐,今日得见真官,是属我之幸事,我这一辈子,活的非常憋屈,从生到死,都不得吐出,内心的压抑感别提多强了,今天见到真官,想一吐为快,不知真官愿不愿听?”
这话很明白,此时说话的,其实是毕家的大小姐,只是毕大小姐说话时所通过的媒介,却是毕二小姐的身体。
路时中说:“愿闻其详”。
女子继续说:“我是毕老爷的前妻所生,而我这个妹妹,也就是毕二小姐是后母所生,由于毕老爷宠爱后母,所以我这个妹妹也自然凭借其母的地位任性妄为,全然不把我这个当姐姐的当回事儿,对我百般羞辱。”
“原本我想,女子吗,总有一天要嫁人的,即便在家中受再多的苦,也会有出头之日,只要一纸婚书,随便哪个男人,都能救我脱苦海,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仅存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这件事是这样的,当年我父举家在京,有媒婆上门提亲,说只要金钗一双,作为信物,既可成婚,可这丫头,坚决不肯,阻挠我的婚事,最终让我嫁人的梦想成为泡影,我当时绝望透顶,感觉暗无天日,心情郁闷到了极点,结果是郁郁而终。”
“我死后,想着重于自由,可转世投胎,再不与这刁钻妹子见面,可不想,鬼差说我名不当觉,坚决不收,将我赶出酆都,导致我成为了孤魂野鬼。”
“后来我魂游四方,有幸得见下凡办事的九天玄女娘娘,受娘娘大恩,可怜我命苦,遂授我还魂之术。”
“得术后我自是欣喜,努力练习,终有小成,可万没想到,就在我即将成功之时,又遭二丫头破坏,导致我在紧急关头,前功尽废,重生无望,做鬼又难出头。”
“我气不过,深敢不幸,于是上了她身,想将其弄死,跟她同归于尽,补偿我这么多年来所受的冤屈。”
“在这里,我仅代表我自己,感觉玄女娘娘的大恩大德。”
“对于您路真官,我早有耳闻,知您是抓鬼的高手,术士中的大师,所治之贵,多为作恶人间的,可是我现在是回来报仇,而且此仇不报,誓不罢休,神档杀鬼,人档杀人,您不要像以前的那些废物道士一样,跟我说什么大道理,这些对我来说,丝毫无用,至于怎么处置,您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女子站在一旁,等待路真官的回复。
路时中听完,沉底良久。他反复思量女子口中提到的那位神仙,也就是九天玄女娘娘,这位女神在中国神仙圈里可是一大亮点,她不仅是符箓派的祖师婆,更是诸多王侯将相的导师,路时中对于玄女娘娘那可真是无边的敬畏。如果眼前这位毕大小姐,真的得到过玄女娘娘的指点,那么作为符箓派小瘪三的路时中,万不敢对这女子胡来,否则回头自己上了天,玄女娘娘问及此事,自己该如何回答?但如果这女子是骗人的呢?可是她口中说辞,严丝合缝,就算真是唬人,也暂时不能动,回头待我查明真相,再做定论吧。
想到此,路时中开口说:“你的理由很充分”。
说完,又转头对毕县令说:“你现在知道上你二女儿身的是谁了吧,也应该为什么要作祟你的二女儿了吧,这属于你们的家务事,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做好你大女儿的工作,你二女儿可能还有救,但要是想通过我的法力去制伏她,着实不是我方士所为,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最好还是由你自己来解决吧”。
话音一落,毕小姐忽然倒地,再抬起时,有如刚进船舱一般,呈半死状。
到此,鬼祟一事真相大白。系姐妹相残,且有九天玄女这么大的挡箭牌,路道士自然不能插手,只能顺其自然,静待结果。
说来也巧,第二日,二小姐便停止呼吸了。或许是毕大姐一直在等待可以诉苦的路时中,将一切交代明白,然后再弄死妹妹,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算明事理,知道妄动杀机并不符合天道,想要报仇也该得到其他人的认可,路时中的认可,促使其痛下杀手。
二小姐死亡报告一出,毕家上下一片悲切,随后布置灵堂,按部就班。放下毕家办丧不表,咱们转回头说说这位路半仙。
路时中得到毕二小姐死讯后,匆忙下船,马不停蹄的跑到路家,名义上是治丧,其实他是想搞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如果毕大小姐真的遇到了九天玄女娘娘,那么,娘娘教给毕小姐回魂的法术,叫什么,是如何练的,当然,现在毕二小姐已死,大小姐的灵魂也可能扩散了,所以具体的练法难以得到,但有一点肯定能有答案,那就是大小姐口中所说,自己的法术被二小姐给破了,虽然得不到修炼的法门,但总能从破法的方式中知道些端倪。报着知道是一点是一点的心态,路时中迈步走进了灵堂。
此时的毕家是招魂幡高高挂起,从房梁到门槛,皆是白绫飘飞,家庭奴仆各个透顶孝帽腰系白绦。
毕县令见路时中前来吊唁,深表谢意,礼貌寒暄后,路时中将话题转向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老路说:“兄弟,别太伤心,人终有一死,不是你我能左右得了的,昨天你大女儿口中说的长期受辱,这本是你家中之事,我不清楚,至于那玄女授法一事,又是你大女儿死后际遇,无人作证,所以我来确认一下,如果玄女真的授法了,那你大女儿必然要练,既然练了,自然有异,而言其法遭到二女儿的破坏,想来你作为本家,整日跟女儿在一起,应该知道是如何破的法吧,如果您告诉,我有幸得知,借我的专业水平来判断一下那到底是什么法术,你大女儿说的话是否属实,也就一切大白了”。
毕县令听出路时中的意思,他明白,路真君一方面想知道玄女娘娘所赐神法的法理,另一方面想确认下大女儿所言是否属实,以期给路真君自己一个交代,否则错放了恶鬼,丧了好人的性命,你岂不是坏了他一世的英明吗。想到此,毕县令决定如实相告。
老毕说:“此前确有怪事,现如今回想,肯定就是它了”。
要说毕县令口中“怪事”是何事?这就得从毕大小姐死后说起了。
话说毕老大含恨而终。由于举家在京,不是故里,所以不得下葬,只能暂且将棺木安放在开封城外一间寺庙之内,美其名曰“太平间”,说白了就是用木头临时搭建起来的房子,将棺木放在房内,但为求不引人注目,在棺木四周砌上了一层砖墙,一方面用以挡住风雨对棺木的侵蚀,另一方就是给棺木一个防护罩,免得盗墓者知道有棺,开棺取物,虽然棺未下土,但死者随葬之物都以俱全,省得日后再费周章。
整个棺材就这样的躺在了“砖屋”之内,在“砖屋”的后面,也就是背对门的地方,留一个小口,足够伸进一只手,方便回头拆砖的时候用。一切弄好,家人离开,只待清明重阳前来祭奠。
一转眼,清明到了,毕家上下打点祭品,前来打小姐的“坟”上拜祭。
刚一到寺院,家人就看到在大小姐棺木所居住的木屋旁边,又搭建起了一间房子,从整体情况看,有屋有窗,干净整洁,该是个读书人的居处。
走近一瞧,但见屋门上闩,说明主人外出,家人自顾去大小姐的陵寝拜祭,可恨了这刁钻好奇的二丫头,偏对居住在大姐陵旁的屋子起了兴趣,抬手卸下门闩,推门走了进去。
也就在二小姐走进房间的一瞬间,她惊叫一声,弄得全家老小也都跟了进来。
原来啊,二小姐一进屋,就发现正对门的桌子上摆放着一面铜镜,二小姐呼叫的原因是,这面铜镜乃是她姐姐的陪葬之物,不知为何竟出现在这间屋子中,由于她年纪尚轻,对鬼神多有不信,所以她心中第一个反应是,此人乃挖棺盗墓之人,定是开了姐姐的棺木,窃取了铜镜。
对于这样结论,毕县令开始是不屑一顾,他认为,这样的铜镜随处可见,更何况京师繁华地,品牌打得响,人手一件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足为奇。
可这二小姐却一口咬定,此镜必是姐姐所有。她说:“这铜镜乃是我跟姐姐一同买的,一人一个,买回后将其装裱包裹,其上所用绵薄纸张,刺绣针织,皆出我手,不信来看纸张,全是父亲大人做名片用的纸质”。
老毕见女儿言之凿凿,又查看了纸张,却是如此,于是不由得慨叹女儿命苦,死时冤枉,死后又遭骚扰,真是可悲可叹。老毕一悲,全家人自然也跟着伤心其来。
正在一家老小痛骂盗贼无耻时,这房间的主人,回来了。
主人一进门,立刻大斥:“书生陋室,一贫如洗,有什么好参观的,你们不请自来,破门而入,还有王法吗?”
毕二小姐本就蛮不讲理,见书生怒斥,心中火起,大呼道:“无耻贼人,还敢提王法,你可知这面铜镜,乃我姐姐陪葬物品,现在竟跑到你的屋中,还反口指责我们,来人啊,将他捆绑,拿到官府法办”。
话音一落,只见三四家丁劈里扑腾的一拥而上,三下两下就将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五花大绑,准备交送官府。
书生一见这架势,哪还敢再兴谩骂,只能跪地求饶,一五一十的将铜镜的来历,娓娓道来。
这事儿发生在半年以前,有一晚书生伴月读书,正沉浸之时,忽闻敲门之声,开门一看,乃是一位如花似玉满面桃花的大姑娘,书生顿觉神清气爽。
问姑娘何故此时驾临,姑娘说:“我是一妇人,因跟婆婆拌嘴,被她赶了出来,本打算回娘家,可问题是娘家在城中,现天色已晚,不敢继续上路,希望暂住一宿,待明早即走”。
书生一听,这不是天赐的好事儿吗,哥们积攒了多年的荷尔蒙,一直蠢蠢欲动,现在有人主动为自己疏导,而且又是位如此漂亮的美妇,简直是天将艳福,无需多言,快请进。
而在那晚之后,这女子每晚必至,时而白天也来,跟书生搭建起了没羞没臊的二人世界。
有一天,书生洗完头,想将头发攒起,但苦于没有镜子,所以一缕一缕的难以收拢,正在手忙脚乱之时,女子赶到,扑哧一笑的说:“没有镜子吧,我这有。”说完,便从包中取一面铜镜,而这面铜镜,正是二小姐口中的大姐陪葬之物。

后来时间一长,更是在生活中把书生照顾得妥妥当当,堪称贤惠女子之典范,书生遂对其动情,想探知她的底细,以期娶为正房。后来几次询问,女子都支吾作答,并不想了然告知,问过几次,书生便觉无趣,也就不再问了。
昨天晚上,女子来房中,对书生说,明日要同家人宴客,一家老小无一例外,必须参加,所以明日不能再见,待后天晚上,方能相见。
公子一早醒来,知道女子已回家中,顿时被一种失落侵袭,郁郁不乐,也无心读书,于是关了房门,去荒郊野外散心,期望尽早度过今年,快些见到女子。
毕县令听完,知是大女儿一灵未寐,鬼魂作祟,经过书生的介绍,一种父女真情,涌上心头,其他人也是伤心。然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听爱情故事的,毕二小姐就是位极理智的人,她对书生的故事一个字都不信,认死了书生乃盗贼,为求证明自己的判断,这孩子呼吁大家,开棺验证,直到现在,毕二小姐都不认为那位送书生铜镜的人是自己姐姐的鬼魂。可见,毕二小姐应该是一位破除封建迷信的先决者,至少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少数中少数了。
毕二小姐一意孤行,率领众人直冲棺木,拆砖拔钉,掀盖探清。
棺内景象另所有人大为震惊,只见大小姐端坐于内,双足互叠,一丝不挂的戴着个男子头巾,自腰以下的肉都是新生,肤质华润,温婉诱人,而腰部往上,却如枯树一般,腐朽难看。
一见此状,所有人都后悔开馆了,要说为什么,这是因为打扰死人乃古之一大忌讳,再说就为了一个铜镜,开馆验证,确实是小题大做的,由此可见,这位毕家二小姐对其姐姐的轻蔑与不屑,已经到了极点,就算是死,都对她毫不尊重。
毕县令似乎也明白过来了,决定将棺木盖好,然后把那书生给放了,不至于为了一块铜镜,扰了女儿的休息。可是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一时糊涂,对二女儿的一时纵容,竟彻底断送了二女儿的命。
至于这位毕家二小姐,就算世间无鬼,以她对自己亲人尸骨的这种做法,对亲人长辈的无视,对自家姐妹的羞辱,也是死有余辜。
【原文】至于玄女授法,其实就是某种可以令人鬼在一起正常相处的法术,人不会因为与鬼亲近而体质渐虚,最终惨死,至于修炼的办法,想来只有鬼才知道,路时中得到的答案,仅仅是破除法术的方法,那就是开棺见日,使重生前功尽弃。
路时中.字当可.以符箓治鬼著名士大夫间.目曰路真官.常赍鬼公案自随.建炎元年.自都城东下至灵壁县.县令毕造.已受代.檥舟未发.闻路君至.来谒曰、家有仲女.为鬼所祸.前后迎道人法师治之.翻为所辱骂.至或遭棰去者.今病益深.非真官不能救.愿辱临舟中一视之.路诺许.入舟坐定.病女径起.著衣出拜.凝立于旁.略无病态.津津有喜色.曰、大姐得见真官.天与之幸.平生壹郁不得吐.今见真官.敢一一陈之.大姐乃前来妈妈所生.二姐则今妈妈所生也.恃母钟爱.每事相陵侮.顷居京师.有人来议婚事垂就.唯须金钗一双.二姐执不与.竟不成昏.心鞅鞅以死.死后冥司以命未尽.不复拘录.魂魄漂摇.无所归.遇.九天玄女出游.怜其枉.授以秘法.法欲成.又为二姐坏了.大姐不幸.生死为此妹所困.今须与之俱逝.以偿至冤.且以谢九天玄女也.真官但当为人治祟.有冤欲报.势不可已.愿真官勿复言.路君沉思良久.曰、其词强.顾毕令曰、君当自以善力祷谢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复困惙如初.盖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其言则大姐之言也.死已数年矣.明日、二姐殂.路君来吊.其父曰、昨日之事.曲折吾所不晓.而玄女授法.乃死后事.二姐何以得坏之.君家必有影响.幸无隐.在我法中.当洞知其本末.毕令曰、向固有一异事.今而思之.必此也.长女既亡.菆于京城外僧寺.当寒食扫祭.举家尽往.菆室之侧.有士人居焉.出而扃其户.家人偶启封.入房窥观.仲女见案上铜镜.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以在此.必劫也.吾以为物有相类.且京师货此者甚多.仲女力争曰、方买镜时.姊妹各得其一.鞶结衬缘.皆出我手.所用纸.某官谒刺也视之信然.方嗟叹而士人归.怒曰、贫士寓舍.有何可观.不告而入.何理也.仲女曰、汝发墓取物.奸赃具在.吾来擒盗耳.遂缚之.士人乃言半年前夜坐读书.有女子扣户.曰、为阿姑谴怒.逐使归父母家.家在城中.无从可还.愿见容一夕.泣诉甚切.不获已纳之.缱绻情通.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昼亦来.一日方临水掠鬓.女见而笑曰、无镜耶.我适有之.遂取以相饷.即此物也.时时携衣服去补治.独不肯说为谁家人.昨日见语曰、明日我家与亲宾聚会.须相周旋.不得到君所.后夜当复来.遂去.今晨独处无悰.故散步野外以遣日.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吾家闻之皆悲泣.独仲女曰、此郎固妄言.必发验乃可.走往殡所踪迹之.其后有罅可容手.启砖见棺.大钉皆拔起寸余.及撤盖板.则长女正叠足坐.缝男子头巾.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肤理温软.腰以上犹是枯脂.始悔恨.复掩之.释士人使去.自是及今.盖三年余矣.所谓玄女之说.岂非道家所谓回骸起死.必得生人与久处便可复活邪.事既彰露.不可复续.而白发其事.皆出仲女.所谓坏其法者岂此邪.路君亦为之惊吒.道出山阳.以语郭同升.升之子沰说.造字以道.《夷坚志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