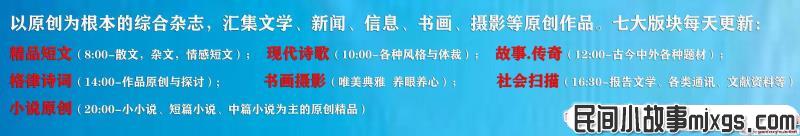

莱阳前河前西周墓群的发现,尤其是墓葬内出现“己侯壶”等青铜器,且又以多名奴隶殉葬,这对墓主人的贵族身份是一些有力的证明。这说明前河前村一带,应该是己国的一个中心,至少是一处城邑。
城池的主人乃是“己国”的贵族。
前河前村至今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在古代的一个晚上,一支身穿白盔白甲的马队,突然来到了这里,被河水挡住了去路,从此就长期住了下来。
在没有发现古墓群以前,前河前村民就一直称村前的高地为南殿,前村人叫西大殿,历史上的传言总有一些缘起,这些遗存到底是否是己国的王宫大殿,便不得而知了。
关于前河前“己国”古墓背后的历史真相,《春秋》《左传》和《史记》等典籍均有“纪候去国”的记载,并记载了一个叫“鄣”的城邑。
对于这个己国的遗邑“鄣”,常兴照、程磊在《试论莱阳前河前墓地及有铭陶盉》一文里,在充分考证史料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作了大胆的猜想。论文说:经籍中明确的已国城邑有四:《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邢、鄱、酃。”庄公三年“秋,纪季以鄣入于齐。”
郑、酈、部、酃乃己之四邑,王献唐先生在《山东古代的姜姓统治集团》一文中已明确考证其方位:部在安丘,鄱在昌邑,邢在临朐,酃在临淄东三数十里。
偌大范围之内,还杂居着莱族势力,王氏喻之为“插花地”。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庄公四年》的记载:“夏……纪侯大去其国。”庄公三十年:“秋七月,齐人降鄣。”公、谷两传皆言:鄣为纪之遗邑。
杜注:“鄣,纪之附庸国”这都说明纪亡之后仍有子遗。
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说:“纪亡之二十余年矣,而鄣犹存,盖守邑大夫,抗节不降,若安陵不人于秦,莒、即墨不入于燕是也。”
关于此鄣之地望,杜预认为在东平无盐鄣城。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鄣字条谓:“今海州赣榆县之北七十五里有故纪鄣城,亦曰纪城。”
王献唐先生详细论证了这两处地方距齐、纪均甚远。如在东平或赣榆,当时中隔鲁、莒、向、邾等国,纪国无法统治,齐人的势力也达不到这些地方而收降纪邑,降之也无法统治。进而推定鄣之地望仍应在纪国外围邢、鄱、鄯一带。
王氏之说有理,但仍没举出更令人人信服的事例来。该论文认为,这个鄣邑应该就是莱阳前河前遗址。
其一,前河前M2所出己器铭文和墓葬形制,证明了墓主人是一个士、大夫之类人物,从前河前遗址的地貌、遗存,亦足可推定为古代城邑遗址。
其二,征之文献,《左传·隐公元年》:“八月,纪人伐夷。”
杜注:“夷在城阳庄武县。”《元和郡县图志》载:“即墨县西五十里有庄武故城,晋张华封庄武侯。”就是说,纪人所伐之夷,当在今即墨县境。自即墨去昌邑、寿光、安丘、临朐,均距离遥远.中隔大沽河、胶莱河、潍河等数条大河,如此远征绝不是十百里,发生征伐可谓举手投足之劳,由此可知其真情缘。
其三,前河前遗址所傍之五龙河的上游,旧志曾名今上去数十里地还有陶漳镇,古代地名同音转借,游移古代是否就称漳河也未必不能。
若如此,则从地理、河前遗址为纪之鄣邑,是可以成立的。
如是推之,以远灰城一带的统治者以及迁居胶东的己族发生媵嫁、交换或战掠等方面的联系(如纪侯鬲出于黄县旧城,己华父鼎出于烟台上夼)就不难理解,甚至“己侯大去其国”的流亡方向也能找到一点影踪了。
上文所讲的“陶漳河”,即现在莱阳市境内的清旁边还有大陶漳、西陶漳两个村子,这里距离下游的漳村东南又有东、西两个城阳村,再往南便是汉代和南北朝时期的昌阳古城(今前、后发坊村)。这一带今为盛产莱阳梨的照旺庄镇,是一片肥沃的河边台地,和前河前台地颇为相似。
根据“纪侯大去其国”的文献记载和莱阳前河前村“己国”古墓群的发现,有学者推测,己国贵族在亡国之后,有可能从山东富庶的内陆地区举族东迁到了莱阳的“鄣”邑,以避齐之难。如是,鄣邑距离即墨不远,“鄣”或许就在前河前村或附近。只可惜,“己国”和“鄣城”的历史过于遥远,地面上已经没有遗迹可寻,“鄣城”在不在莱阳境内的间题,暂时只能存疑了。
(整理:唐风新月)
历史资料
纪文侯姜静
鲁隐公时代和鲁桓公初年,鲁国国势极盛。尤其是公元前699年,鲁国、纪国、郑国联军大败齐国、宋国、卫国、南燕国联军,此战终结了"齐僖小伯(霸)"的局面。纪国得以安定一时。鲁桓公趁势于公元前695年,在鲁桓公、齐襄公和纪侯三国君主的盟会上试图使齐国和纪国和睦。然而同年,齐国军队侵犯鲁国边境,边境上打了一仗。说明鲁桓公的调解失败。第二年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和郑君子亹被齐襄公杀死。鲁郑两国顿时不及考虑保存纪国。形势急转直下。
公元前693年,齐国军队驱走纪国的郱、鄑、郚三邑居民,占有三邑土地。公元前691年,纪国分裂。纪侯之弟纪季以纪国的酅地投降齐国,做齐国的附庸。同年鲁庄公试图和郑君子婴商量保全纪国,郑君以国内部不安定为由拒绝。公元前690年,齐国军队攻破纪国都城。纪侯将剩下的国土交给纪季,出国逃亡一去不返。纪国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