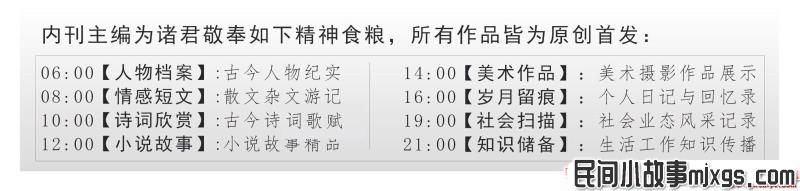

春耕前,县里三级干部会议一结束,从青龙通往秦皇岛的班车上下来的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带着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进了沟。当晚,以小队为单位的社员会议在各村的饲养院里一直开到半夜,月升中天的时候,几乎连呀呀学语的娃娃都知道了一个新名词:杂交高粱。
山坡上种的高梁品种确已很古老,其中有几个品种还是日伪时期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种,象牙白高粱就是其中一种。象牙白高梁是真正含义上的“高”梁,秫秸杄儿一丈四五高,成熟的时候那晃晃悠悠的细杆儿尖上顶着像乡村小学老师常留的分头一样的长而且细地向四边瀑垂的码子,几十枝码子上拢共才能结三四百粒高粱籽儿,论分量不过四两半斤。日伪时期稻米是军需品,中国人不让吃大米,这种白高梁米就是当时的主粮,叫做文化米。这种高粱磨出来的秫米晶莹透亮,煮出来的粥表面上浮着一层油皮,米汤又稠又粘,这已经是这个虽然低产而品质尚优的品种终于被保留下来,成了山里人认可的细粮。
这个似乎还带着民族耻辱的品种却没有像民族耻辱那样渐渐地化解消贻,却实实在在的留在这片关外山野间的土地上,被这里的人们年复一年的留下了种子,再播种到那瘠土中,耕锄收场的期待着那每亩一百多斤的收成。
县里这次三级会议的精神就是在全县范围内更换低产的高梁籽种,统一种植我国农业学家新培育出的高产品种晋杂5号,旨在提高山区的粮食亩产量,让山里人能多分到一些度日的口粮。
山里人的口粮也真是少得可怜,一年的耕作,秋后分到的粮食不足三百斤。再磨去两个多米的糠壳,大约只剩下两百四五十斤能入口的粮食,这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命粮。
口粮少,活计重,再加上锅里缺油少盐,在青龙这片山里你能体会到最原始含义的饥饿。多打些粮食意味着生存质量中最基本元素的提高,意味着远离饥饿的春荒夏荒,意味着那些细脚伶仃挺着被稀粥灌大了肚子的孩子能有一口正经粮食果腹,意味着那些古稀老人不再吃那些在河水里浸泡后去掉氢氰酸的野山杳叶子,不再手挽着荆条筐仰立在山坡上等着风把那橡树上的橡子吹落下来,捡回家去磨粉充饥。
人们相信这种亩产八百斤的高梁晋杂5号能够让每家锅里的稀粥变得再稠一些,能够在转年新粮下来之前,墙角上那口每年到这个时节都是空荡荡的板柜里还能剩下半斗八升的粮食。
有了粮食,山里的穷日子就能好过一些难怪有些人家在高兴的夜不成寐时,计划着今年秋后如果多分了一两百斤粮食,当天就去龙王庙集上捞个猪羔子养上。足足的粮食糠喂它四个月,到了腊月底怎么也养成个百十来斤。杀了猪能炼几斤荤油,猪肉扛到集上一卖,也能挣出买三个猪羔子的钱,归到圈里再养上,反正咱快有粮食喂它了。剩下的头蹄下水把大小队干部都叫来,人家给咱淘换来这能多打粮食的种子,理应请人家喝顿酒,剩下的汤水全家人还可以过一个好年。
被饥饿折磨的几近木然的山里人难得有这样高兴的事,这几天但凡打头碰脸时议论的都是杂交高粱晋杂5号的有关事情。有人说大队干部这回开会时见到过这种高梁,那高粱头足有葫芦头子大小,密密麻麻的里外都是码子,那高粱粒子也比象牙白的粒子大了不老少,个高梁头子就有两三斤重。
有人又说这杂交高梁种稀了不中,绑定得密植,行距一尺,株距也就是两三寸才好。还有人说这杂交高梁不怕地荒,就是草围了脖子也照样打个八百斤望上,早种几年杂交高粱的地方是撒了种就完事儿,也不耪也不耠,那里的人光闲着,不象咱这地方人这么累。
在这很难看到甚么希望的穷乡僻壤间,这些带着希望的传说就像一茬一茬的山杏花,一夜之间开了个漫山遍野。
耕地了,小队长杨青林把半口袋从大队领回来的杂交高粱种子搁在地头上,仔细的捻了捻手心里摊开的高梁种,喃喃的说了句:“这高粱的糠可有点粗啊。”杨青林是这庄里的好庄稼把式,平常队里的耕耪收场大小农活都是他拿主意,没人敢和他理论甚麽。
可这一次却惹了众怒,一时间:“你懂个鸡吧啥呀,这是县里发下来的优秀种,那还错得了!”
“你见过这高粱?你也是这辈子头回见吧?”
“县里那一大院子的干部就不如你?那你咋不当县长?”
杨青林一时语塞。
地耕完了,夜里悄悄潜来几场好雨,山坡地上墒情好得不能再好,杂交高粱的苗出得特别齐。
行距和株距没有像传言中的那般密,这也没啥,总比象牙自高粱要密实得多。跟着高粱苗一起长出来的杂草还是要糖掉的,通常的三遍地一遍也不能少,要不山里人闲着干吗?
糖完三遍地以后还是要用耠子趟出垄沟垄台儿来,一是盖死了残留的杂草,二是苗根儿上追了化肥以后必须培土保肥。人们不再记得耕地前自己说的那些眼见着已经失实的话,只是把心思转到杂交高粱萌出的像扛了枪似的最后一枝叶片上。高粱扛枪,吐穗灌浆,等上几个月,粮食进仓,这山里的农谚给了山里人一次久违的希望。
榜三遍地前后又下了一场透雨、这一年真是难得的好年成。粮食进场了,从十几条山沟里往外挑高粱头子捆的人缕缕行行的奔场院汇集过来。这杂交高粱的穗头子真的很大,每个穗头子足足有一尺二寸,里里外外都是密密的码子、那码子上的高粱粒子像后山坡上的樱桃棵子上的野樱桃一样结得一串串的。
往年一搂粗的高粱头子捆也就是三十多斤,尖扁担一头一个的挑回场院,一路上不觉得累。这杂交高梁的穗子要重了许多,同样粗的两个捆子加上扁担足有一百三四十斤,压得人肩膀上火辣辣的被压得哈嚓哈嚓的人进了场院,把那沉甸甸的高粱头子捆扔到地上,总还忘不了说上句:“好家伙,真他妈死沉死沉的,我看这高梁就是没种错。”
庄里的几个精明人围着队长杨青林絮叨:“估产别估太高,悠着点望上报,好不容易多打点儿粮食,报高了都交了公粮,百十口人这一季又瞎忙活了!”
杨青林心中有数:“那每亩咋也得比象牙白多报个几十斤呗,要不你能交代得过去?”
内部估产,杂交高粱亩产八百九十斤。对上面报产,亩产四百来斤。说是今年风不调雨全队的骡马都拉上碌碡在场院里转着圈的压场,全庄的男女老少都在场院里边忙活着。
秋场是庄稼人喜庆的好日子,对拉碌碡的牲口来说打场也是个累活计,凡是打场的牲口一律不戴笼头,场上的粮食有的是,想吃就吃,也省得回饲养院还得喂料。
三匹戴着蒙眼的骤子拉着碌碡进了场,一时去掉笼头约束的牲口踏上那铺得厚厚的高粱穗,低头用那灵活的唇舌叼起一个沉甸甸的杂交高粱头子,一边在吆喝声中继续转着圈子,一边大嚼起这刚打下来的新粮食。
丰收了,牲口也有了丰足的草料这一冬吃满了膘,明年耕地时也好干活计。
嘴里叼着高粱头子的骡子打起响鼻,原本已叼在嘴里的高粱头子掉在地上,又和那满场的穗子浑然难辨了。三匹骡子奇怪的甩着头嘴里的涎水被吹得泛起白色泡沫,滴滴答答的流在那铺得满场的深紫色高粱穗子上。
队里最诡道的武贵诧异的喊着:“哎,这骡子咋不吃了,今儿个早上许是料喂多了?”
边说着边拿起一个高粱头子凑到一匹骡子嘴边,那骡子只用鼻子闻了闻,一拨拉脑袋,在缰绳上的铜环叮当声中,那个硕大的杂交高梁穗子儿被甩落到地上。
蹲在场院石墙上的队长杨青林,手里拿着一个高粱穗儿,一个一个的往下揪高粱粒,又一个一个的填进嘴里慢慢的嚼着。须臾间,他突然站起身来:“这是啥鸡吧粮食,又粗又麻嘴的,一点油性也没有。”
场打完了,依然怀着希望的人们把高梁炕干,磨去了糠,几乎全庄人家的锅里都煮上了这杂交高粱粥。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小队饲养院的连五间的屋子里站着坐着的挤满了没等队长招呼就到了的庄里的男女老少。昏暗的煤油灯那如萤的光线下,影影绰绰的看见队长杨青林在墙角的柳条斗子上低头无语的坐着。
在那满屋的噪杂声中隐约能听清这样的几乎是吼出来的话:
“光多打粮食有甚么用?这XX粮食还不如象牙白高粱的糠好吃!”
“牲口都不吃,这算啥优秀?”
“队长啊,你让用这高梁喂驴,那驴都不拿正眼瞅,你说我这饲养员咋干!”
“我家的鸡吃了几天这高粱都歇蛋了,这叫啥玩意儿啊。”
“我家那猪都不喝搁了这高粱糠的泔水,一个劲的在槽子边上磨嘴。”
杨青林终于说话了:“都闹啥,不能吃就交公粮。”
半个月后,公社粮站门前贴出告示:今年交公粮一律不收晋杂5号高粱。
才修好的猪圈依然空荡荡的,今年龙王庙集上猪羔子的价钱降了又降,还是少有人问津,总不能买回这些不吃杂交高粱的畜生,去抢了人的食吧?喂了这杂交高粱的母鸡真的歇了蛋,山里人那用来换洋火和食盐的唯一经济来源也中断了。
原想过年时请大小队干部的事自然也没了着落,炊烟缭绕的小山村里,每家的锅里煮的都是这黑紫色的高梁粥。那些木然的山里人又木然的吞下那不再浮着一层油皮的已经变得苦涩难咽的高梁米粥。
那似乎永远也煮不烂的杂交高梁在孩子和老人的嘴里辗转嘴嚼着被吞下肚子。蹲在墙角的孩子那脏兮兮的小脸上挂着泪水,嘤嘤的哭泣着,吃力的排出不成形却依然粗糙如刀的紫黑色排泄物。
个多月以后,孩子们的细小幼稚的牙齿上出现了一条黑紫色的沉着线,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丰收了,收获的当然是粮食,是那亩产八百斤的杂交高梁。县里通知:明年要在全县加大晋杂5号高梁的播种面积。
山里的冬天来了,那满地的薄霜上边又覆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
四年后,我到医科大学就读于医疗专业,从教课书中读到了那曾经沉着在山里孩子乳牙上黑紫色的线是慢性铅中毒的诊断依据。
十六年后,某报发表了山西省农科院良种培育所的一篇报告文学,报告中以忏悔的笔触写到:我们在培育晋杂5号和晋杂57籽种时,只注重了作物的高产品质,忽略了作物的食用性质,在此我们谨向当时种植如上两个品种的农民同志深表歉意。
(作者:莱阳/杨树湾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