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园之鬼
江宁有明代中山王徐达的旧居,明朝灭亡后,徐达的祠堂也被毁。中山王旧居一分为二,东边做了官府仓库,西边成了布政司公署。两个衙门隔开,各自开辟了小园,因为房子旧,分别起名为适园,瞻园。后来被粤寇的一个头目占据,某人本是广东的海盗,养了几十个侍妾,夏天经常和侍妾们裸身在园中淫戏。

一天晚上,他正和一个侍妾在亲热,忽然听到另一个侍妾那里也传来猥琐的声音。某人大怒,起来去看,原来另外一个侍妾那里有个和自己面貌、穿着、声音都完全相同的人。二人格斗起来,两个女人也分别帮着自己身边的男人。打了好一会,天快亮了,那个假的厉声说道:“你欺人太甚,明天中午我们到金柱、玉溪那里再斗。”金柱关、玉溪口,是芜湖附近的港口,距金陵一百多里。
第二天早晨,上峰派某人在城墙上领兵防御官军。他为昨晚的事惴惴不安,但是到了中午,也没什么异常情况出现。傍晚回家也平平安安的。但他始终是心存顾忌,放荡的行为收敛了很多。过了几天,又轮到他在城墙上值班,忽然看到南面来了一个东西,像车轮那么大,形状像张开的雨伞。那东西把某人抓去,扔到了玉溪口。他被摔的遍体鳞伤,但性命无碍。这时来了一个黑头陀,强行把他收为徒弟,在五岳间游历。后来,叛乱平定,黑头陀也不知去向。某人拿着师父的身份凭证潜回了石城。
有一天,他在一个小巷子里遇到了一个以前的侍妾,这个妾已经沦落为娼妓。她看到某人后,念旧情,把他领到妓院,留起头发。又一天,被湘军中的一个老兵认了出来,抓捕到兵营,审讯后处斩。那个侍妾贿赂了行刑的人,去见了最后一面。某人嘱咐她道:“只要把我葬在太湖石笋旁,我就知足了。”那个地方是是官府资产,侍妾假说兵乱前本是民家产业出重金赎了出来,把某人葬在了那里。
【原文】江宁有明中山王徐达之邸,明社既墟,徐祀亦斩,邸析而为二,东为储廨,西为薇垣。两衙衡宇相望,又各辟小园,略因其旧,道署曰适园,藩署曰瞻园。粤寇之酋曾据之。酋,粤人,故海盗,蓄姬十数,夏夜恒裸逐园中,为迷藏戏。被持者就露草淫之,一夜遍数十人,日以为常。
一夕,酋与某姬狎,闻他姬有媟亵声,大怒,奋起逐之。其人与己面同身同,声音亦同,迷离扑朔,两相格斗,姬亦助殴。已而天将晓,伪者厉声曰:“汝逼人太甚,翌午相见于金柱、玉溪间可耳。”
金柱关、玉溪口,芜湖之近港,距金陵百里而强。诘旦,酋被命,登城御官军。日逾午矣,窃幸无事。薄暮归,亦无他变,然亦稍稍敛迹。越数日,又值登陴,瞀然自南来一物,大如车轮,张如雨伞。酋当之,被摄去,落玉溪口。时犹未晡,身遍鳞伤,而不死。遇一黑头陀,为披薙,随之走五岳间。乱既定,黑头陀亦化去。酋承其衣钵,潜入石城。
一日,遇故姬某于秦淮曲巷,盖已隶娼籍矣。姬见而怜之,因为蓄发,栖留妓院。一日,为老湘军某所诇,执送营务处,讯明斩之。刑时,姬贿左右,往求遗嘱。酋曰:“葬我园东隅太湖石笋侧足矣。”姬因出重资,购太湖石所在地于粮署吏而葬之,诡言乱前本民家地,应许民家赎也,旋得官许。今其地为民家所有,在四福巷左近。
鬼书净业庵三字
扬州仓圣祠在姜家墩路西。有个四川和尚把仓圣的的塑像运到江南,安置在乐善庵,乾隆己酉年,迁到这个祠里。这年秋天,仓圣祠的台阶下长出了灵芝,红色,像手掌那么大。
在祠堂旁边,还有个净业庵。下面就说说这个净业庵的由来。康熙年间,有个富家女熟读佛典,擅长刺绣,绣了很多佛像。一天晚上,她关上门要休息,忽然看到一个方脸长胡子的和尚,头戴一个斗笠,手持一根锡杖对她行礼。
富家女大惊询问,和尚不回答,呵斥也不离开。她就想喊人,却倒在地上发不出声音。那和尚旁若无人的坐到床上,摘掉斗笠,脱去衣服,盖上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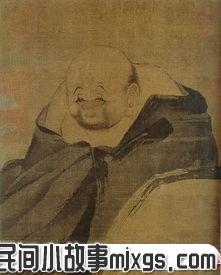
过了好一会,把床前的帘子也放了下来,接着又披上衣服起来,把桌子上的灯吹灭。再次回到床上,不一会就呼呼的睡着了。打鼾的声音像雷一样,中间还夹杂着梦话。半夜时分,这和尚还起来上了一趟厕所,就像富家女不存在一样。快天亮的时候,和尚不见了。富家女这时太能发声呼救。家人赶来,看到床铺整齐如初,唯独帐子上用淡墨横写着“净业庵”三字。拂拭一下,字迹像灰尘一样飘散消失。
四十年后,这个富家女的丈夫和儿子都先后去世,她就出家为尼,在姜家墩路南建了一个尼姑庵居住,起名叫“净业庵”。女子死后,还有一个弟子在那里,到了乾隆己酉年,净业庵又改成了史公祠。

【原文】扬州仓圣祠在姜家墩路西。蜀僧大岩自巴州得仓圣像,供奉入江南,居乐善庵,乾隆己酉,迁于是祠。是秋堦下生芝草,大如掌,赤色。有净业庵在仓圣祠旁。康熙朝,有富室女通佛典,善刺绣,所绣佛像至多。一夕,闭户将就寝,忽见一僧持锡杖,戴斗笠,方额长髯,来前礼拜。女惊问之,不答,叱之,不退走,则张袖遮之。欲呼,口噤不出,倒地昏死。移时复苏,视之,见僧坐于牀,方脱笠解衣裤,坐己被中。
良久,放帐幔。复起,披衣立案前,灭火。复启帐,放帐,帐钩叮当有声,牀笫咿哑,如不胜载。少顷,齁齁然鼻息出入,如巨雷,或咥唔,或梦笑。良久,转身泠泠若溺,溺毕复睡,良久杳然。时天渐明,女股栗,大呼。家人往救之,牀幔安贴如故,惟帐幔有淡墨横写“净业庵”三字。拭之,如灰而灭。迨四十年后,女之夫子皆亡,薙发为尼,乃于姜家墩路南建庵自居,遂名曰净业。女死,惟一女冠子守之。乾隆己酉,即庵屋改建史公祠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