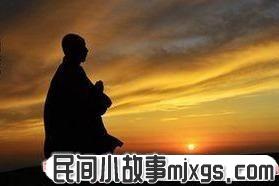枯与荣
药山禅师有两个弟子,一个叫云严,一个叫道吾。
有一天,师徒几个人到山上参禅,药山看到山上有一棵树长得很茂盛,旁边的一棵树却枯死了,于是药山禅师问道:“荣的好,还是枯的好?”
道吾说:“荣的好!”云严却回答说:“枯的好!”
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小和尚,药山就问他:“你说是荣的好,还是枯的好?”
小和尚说:“荣的任它荣,枯的任它枯。”
禅师说:“荣自有荣的道理,枯也有枯的理由。我们平常所指的人间是非、善恶、长短,可以说都是从常识上去认识的,都不过停留在分别的界限而已,小和尚却能从无分别的事物上去体会道的无差别性,所以说‘荣的任它荣,枯的任它枯’。”
无分别而证知的世界,才是实相的世界。而我们所认识的千差万别的外相,都是虚假不实,幻化不真的,甚至我们所妄执的善恶也不是绝对的。好比我们用的拳头无缘无故地打人一拳,这个拳头就是恶的;如果我们好心帮人捶背,这个拳头又变成善的。恶的拳头可以变成善的,可见善恶本身没有自性,事实上拳头本身无所谓善恶,这一切只不过是我们对万法的一种差别与执着。
禅的世界是要我们超出是非、善恶、有无、好坏、枯荣等等相对的世界,禅的世界是要我们在生死之外,找寻另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知易行难
唐代鸟窠道林禅师九岁出家,初随长安西明寺复礼法师学《华严经》和《大乘起信论》,后来学禅,参谒径山国一禅师得法,并成了他的法嗣。
南归后,道林见杭州秦望山松林繁茂,盘曲如盖,便住在树上,人们遂称他为“鸟窠禅师”。
元和十五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白居易对禅宗非常推崇,听说高僧鸟窠住在秦望山上,非常高兴,决定抽空上山探问禅法。
一天,白居易上山来参访鸟窠禅师。他望着高悬空中的草舍,十分紧张,不由得感慨:“禅师的住处很危险哪。”
乌窠禅师回答道:“我看大人的住处更危险。”
白居易不解地问:“我身为要员,镇守江山。有什么危险可言?”
鸟窠禅师回答说:“欲望之火熊熊燃烧。人生无常,尘世如同火宅,你陷入情识知解而不能自拔,怎么不危险呢?”
白居易若有所思,又换了个话题,问鸟窠禅师什么是佛法大意。
禅师回答说:“诸恶莫做,众善奉行。”
白居易讥笑说:“这话连三岁小孩都知道。”
鸟窠禅师说:“虽然三岁小孩都知道,但82岁老翁却未必能做到。”
白居易豁然开朗,施礼而退。

即心是佛
“即心是佛”是马祖学禅的心得。马祖俗姓马,四川人,法号道一,“马祖”是中唐后弟子们出于对道一法师的敬重而称呼他的。他曾在福州入弘禅宗,普度众生。
各地出家人都很仰慕马祖。有一次,一位名叫法常的和尚从大梅山来见他。
马祖问道:“你来这里有什么事?”
法常答道:“我来求佛法。”
马祖又问:“求什么法?”
法常恭敬地说:“向你请教!”
马祖合掌,接着又合眼,嘴里吐出四个字:“即心是佛。”
法常听了,顿时开悟,谢过马祖,回到自己平时参禅的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马祖想起了法常,就派一位弟子前去探望,看看他对“即心是佛”四字是否真正悟通。
弟子找到法常,一进门就看见法常在专心参禅,于是开口便问:“禅师,你从前在马祖那里曾经得到什么见识?”
法常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合掌合眼,一心参禅。
弟子见法常聚精会神,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就大声喊:“马祖过去跟您说过什么?”
法常答话了:“即心是佛。
弟子叫了一声,接着又说:“马祖现在说‘非心非佛’,不再说‘即心是佛了’!”
法常听罢,长叹一声:“这个老汉捉弄人,让他‘非心非佛’吧,我还是‘即心是佛’。”
弟子回见马祖,把法常的情况细述一遍。马祖感到法常悟得透彻,脚踏实地,心不受扰,不禁合掌欢喜,对众弟子说:“梅子熟了!”
此话一语双关,表面上是说法常所住的大梅山上的梅子已成熟,暗中却指法常的功夫已经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