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火日
太史曹来殷某日大白天在京城的家里睡觉,梦见一个很风光的男子向他行礼,自称“黄昆圃先生”,然后把他拉到一个地方,只见一处很豪华的宫殿,殿上坐着一位神祗,面貌端严,衣服的样式是本朝的,就让曹太史觐见,对他说到:“我们三个人,都是入了翰林再做官的,因此只算是前后辈,不必行上下级之间的礼仪。”等曹太史坐下之后,又说:“你在11岁的时候,曾经干过一件大好事,上帝知道了,所以特地把你招来到这里任职,你现在就来吧。”曹太史一片茫然,哪里还记得年幼时做过什么事情呢?再三推辞,说自己家里孩子小、全靠自己负担,所以不愿意来就职。那位尊神就很不高兴了,转过去对领路的黄昆圃说:“你再劝劝他。”然后就拂袖而去。
那个黄昆圃就对他说:“嘿嘿,我也知道做翰林很清苦,你干嘛留恋那个位子不过来呢?”曹太史就苦苦哀求了半天。黄某就说:“我试试看去为你说情,也许能够免掉。但你记住,以后但凡碰到『火日』,决不能出门,千万别忘记啊!”曹太史就问:“那尊神是谁啊?”回答说:“张京江相公。”又问:“在哪边任职呀?”回答:“天庭的都察院。”曹某大惊,就醒过来了。后来每次出门,必定先翻翻黄历,但凡看到黄历上说的是火日,哪怕是红白喜事,也绝不出门。不过时间过了几年,也就慢慢疏忽了这个事情。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腊月二十三日,舍人严冬友邀请曹太史去程鱼门家参加诗会。而这一天恰好是民俗里祭祀灶神爷的日子,于是就以此作为诗题。席间,酒过三巡,曹某迷迷糊糊的就睡过去了,眼睛一闭,身子就软了下来。客人们大惊,还以为是他们的诗词里有不敬灶神的语句,灶神发怒呢,就赶紧一起向炉灶参拜求情。到了三更时分,曹太史才醒来,自己说:“是个黑袍人送我回来的。”第二天,拿来黄历一看,这一天就是所谓的“火日”。

原文
曹来殷太史在京师昼寝,梦伟丈夫来拜,自称“黄昆圃先生”。拉至一处,宫阙巍然,中有尊神,面正方,着本朝衣冠,请曹入见,曰:“吾三人皆翰林衙门官,只行前后辈礼,不行僚属礼。”坐定目曹曰:“卿十一岁时曾行一大好事,上帝知之,故特召卿到此受职,卿可即来。”曹茫然不记幼所行何事,再三辞,力陈“家寒子幼,故不愿来”。尊神甚不悦,旁顾昆圃先生曰:“再向彼劝掖之。”语毕,不顾而入。
先生拉曹笑曰:“我深知翰林衙门亦甚清苦,卿何恋恋不肯来耶?”曹复哀求。先生曰:“我且为卿说情,似亦可免,但卿此后逢火日不可出门,慎无忘也。”曹问:“尊神何人?”曰:“张京江相公。”问:“何地?”曰:“天曹都察院。”曹惊醒。后每出门,必检视黄历,遇火日,虽庆吊事,皆不行。数年后,不甚记忆。
乾隆三十三年腊月二十三日,严冬友舍人邀曹至程鱼门家作诗会,俗以此日祀灶,遂以为题。席间酒数巡,曹伥然如睡去者,目瞑身仆。群客大惊,疑诗中有侮灶神之语,故神为祟,乃群向灶礼拜祈请。至三更时,曹始苏,自言“见黑袍人送我回来”。次日,取黄历视之,二十三日,火日也。
陈紫山
与袁枚先生在乡试和会试时同榜登第的陈紫山,名大蕰,江苏溧阳人。陈紫山初入县学的时候,年方十九。有一次,他突然生了病,愈来愈重,梦见一位穿着紫衣的和尚,自称是玄圭大师,握着他的手说:“你瞒着我来到了人间,还不如回去吧!”陈紫山还没有答话,那和尚又笑着说:“别急,别急,你在人间还要中进士、入翰林院,等享用了再来也不迟。”和尚又掰着手指计算,叹惜道:“这一别, 又要过十七年才能再相会。”说罢就走了。陈紫山惊而醒,出了一身热汗,病就好了。
乾隆四年(1739),陈紫山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官至侍读学士。到三十八岁那年秋天,陈紫山患了病疾,久治不愈,因此想起从前在梦中和尚约他十七年后相会的日期,自知这病是不会好了,就笑着对家人说道:“十七年的期限已经到了,可玄圭大师还没有来接我,可能改期了,这样我又能多活几年。”
有一天早晨,陈紫山起床后,忽然焚香祈祷沐浴斋戒,又叫家人取来冠带朝服,穿戴整齐,对家人说:“玄圭大师已来接我,我要去了。”同榜进士、翰林院编修金质夫,前来探望陈紫山。金质夫素来笃信神佛,在一旁大声喝道:“既然送他到世上来,又要把他拖回去,来来去去,是什么缘故?”这时候,陈紫山已迷迷糊糊,闭着双眼。听了金质夫的一番话,就挣扎着坐起来,睁开眼睛,说道:来时无碍,去也无妨,人间天上,一个坛场。”说毕,盘腿坐定,一会就断了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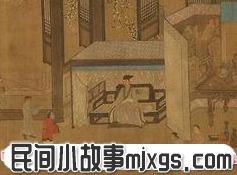
原文
余乡会同年陈紫山,名大㫻,溧阳人也。入学时,年才十九。偶病剧,梦紫衣僧,自称“元圭大师”,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间,盍归来乎?”陈未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琼林一杯酒,瀛台一碗羹,吃了再来未迟。”屈其指曰:“别又十七年了。”言毕去。陈惊醒,一汗而痊。己未中进士,入翰林,升侍读学士。
三十八岁,秋痢不休,因忆前梦十七年之期,自知不起。常对家人笑曰:“大师未来,或又改期,亦未可知。”忽一日早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着之,曰:“吾师已来,吾去矣。”同年金质夫编修素好佛者,在旁喝曰:“既牵他来,又拖他去。一去一来,是何缘故?”陈目且瞑,强起张目答曰:“来原无碍,去亦何妨。人间天上,一个坛场。”言毕,跏趺而逝。
朱法师
袁枚先生在翰林院时有个同僚朱沄,他的父亲朴庵先生,陕西人。朱朴庵先生年轻时,以设馆教授幼童为业。有一次,他偶然经过一个村庄,村里人都争相传告:“朱法师来了。”各家都备下酒菜,请他赴宴;又都请他题名,说是用来镇压鬼怪。

朱朴庵先生笑着告诉这些村民:“我不过是个教授幼童的教师先生,不是什么法师;而且也从来没有什么法术,不能镇压鬼怪,你们要我题名,究竟做什么用呢?”众村民说:“我们村里有个狐仙,为害百姓已经三年了。昨天,狐仙在高空中说:“明天朱法师来,我要回避他。今天先生来,果然姓朱,所以认为您是法师。”朱朴庵先生为他们题了名,这村里果然就太平了。不多久,朱朴庵先生来到了另一个村庄。这村里的人也像以前那个村一样欢迎他,而且说:“狐仙说过:二十年之后,与朱法师在太学的崇志堂相见。”那时候,朱朴庵先生还是一个秀才,连乡举都没有参加过。后来,朱朴庵先生在壬子科的乡试中中举,被选为国子监助教。到任之后,他发现监中的祭器早被狐仙盗去,主管祭祀的因此惶惶不可终日,到处寻找,终无所得。正要议个价钱賠偿,朱朴庵先生想起“二十年后在太学的崇志堂相见”的话,于是写了一篇祭文,请求狐仙帮助。一天晩上,那些失去了的祭器,全都在崇志堂出现了,件件丝毫无损。朱朴庵先生掰着手指一算,他离开从前的那个村庄,正好已经二十年。
原文
同馆翰林朱澐之父朴庵先生,陕西人也,少时课徒为业。偶至一村,村人传呼曰:“朱法师来矣!”具酒馔求书姓名,以为镇压。朱笑曰:“我乃蒙童之师,非法师也。且素无法术,不能镇怪。汝辈何为?”众人曰:“此村有狐仙为民患者三年。昨日空中语曰:『明日朱法师来,我当避之。』今日先生来,果姓朱,故疑为法师。”朱写姓名与之,某村果安。
未几。朱别过一村,其村人之欢迎者如前,且曰:“狐仙有语,二十年后,与朱法师相见于太学之崇志堂。”朱其时尚未乡举也。
后中壬子科举人,选国子监助教。监中祭器久被狐窃去,司祭者皇皇然,索而弗获,方议赔偿,朱记前语,为文祭之。一夕,俎豆之属,尽横陈于崇志堂,丝毫无损。屈指算之,距到某村已二十年。
《子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