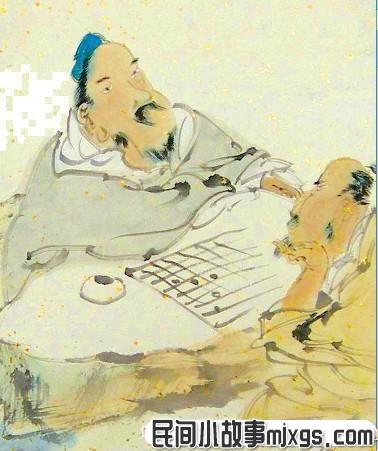
莱阳城西视稼楼赵家,康熙年间出了一个大翰林赵骧,晚年正值嘉庆年初,因饱学,被选入宫,做了太子之师。
他调教很严,每每太子误了功课,必责打不怠,太子乃至尊玉体,从来娇惯,自然吃不住打,便在母后面前诉苦,皇后必疼孩子,便亲至御书房,找翰要求情,并言道:反正不管念书多少,太子都能当皇帝,何苦让他这般受罪。
老翰林正色道:皇后所言不差,可太子学得好了是明君,学得不好便是昏君。
皇后听了哑言,从此后再也不敢袒护。
教了七八年后,人也老了,便告退隐。
太子当时还没长大,心里高兴。
接着换了新任教师,据说是江南明水人,他可与老翰林不一样了,把太子当成了眼珠子,见太子的书房里只有太子师的椅子,没有学生的坐位,便上奏折,与太子打了颠倒,从此后清庭有了新规矩,太子坐着,老师站着,此俗传入民间,一直到今天。
后来嘉庆当了皇帝,执掌国政,日理万机,自然很少再想起老翰林。
当时海外列强已逐渐强大,日、俄及英都与中国有了交往,朝庭自然也不敢太过自大,远方使都来访都有礼相待。
一般外国使者送来国书都事先翻译了,成了汉文。
有一次日本使者来访,国书呈上御览。
嘉庆的左右接过国书。
该国书内容大致是:
中日自古友好,合睦共处,今特遣使者代理朝拜云云,另外台澳之地患海盗古已有之,是故民心过恐,竟将我帮皇侄太郎之游船截劫,至今下落不明,仰仗皇上神威,使人舟归国,不胜拜谢。
值时官把信展开,朗声念来,满朝上下无不听得仔细。
正念到好处突然卡了壳,顿时憋得脸发红。
你道为何?原来这值时官负责的是皇上的文书,都是些学问至深的学者,今天丢了丑那还了得?
嘉庆知道他是遇上了生字,信口说道:举来我看。
这一言既出,双班文武中便听谏官翁声齐起。
原来古时谏官专门督查皇上行径,若有不妥,谏官有权提醒,谏官更晓得大臣不识之文字,未经科物文章的皇上更难知之。若硬接过来,辩认大多也不能清楚,将使国体受辱,故而戒言,民间称之为戒言官。
皇上话已出口不便收回,接了国书一看,果然此字古僻生涩,毫无头绪,不由得在金殿之上沉吟起来,急得台下大臣直冒汗。
原来这翻译文书的日本人也精通汉文,并博览群书,文书中的字来自汉人杨雄的《XX赋》。
嘉庆看了又看,忽然茅塞顿开,想起小时候老翰林曾讲过这字,并为此挨了三戒尺,便给文书一讲,这才解了围。
下朝后,嘉庆思想起启蒙老师,这才深感太师严厉之教诲,为自己的不学追悔,忙刷一旨,着钦差火速去莱阳请太师赴京,以面谢师恩。
钦差去了老翰林家,宣了圣旨,当然不能道其中原委,太子师听后心想,当初对太子要求太苛刻,惹得太子生了气,所以回家后再也没见太子提起,如今忽然宣我入京,必定是要报鞭笞之仇了。
思之再三,觉得凶多吉少,如随京中必尸骨落他乡,不如现在了结了的好,于是吞金而亡。
钦差见翰林死了,忙入京覆命。
嘉庆得知,心中大悲,哭了一夜,定要亲自参加老师葬礼,但国事重大不易动身,所以就派了新科状元为致祭官,代皇上为太师下葬。
状元披素来到了县城,前锋报信的到了视稼楼,赵家人一听新科状元来了,愁得没法,因为家底太薄,招待不起,于是谎称:状元气派特大,恐招来众人,将百姓的青苗踏伤,所以请免。
状元一听有理,也就不勉强,打马回了京,嘉庆大怒,竟将状元斩了——因他违抗君命。
后来皇上给视稼楼赵家赐了匾:太师府,赏了他家人不少银两。
(原创首发 作者: 赵松枝 高风堂 图: 赵磊)

